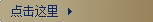作者: 李常永律师、李潜律师
案情
天津市J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4年2月某日六时许,被告人W某无证驾驶无牌照的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在某公路由北向南行驶途中,其车右前部撞上Z某身体,致Z某急性重型内开放性颅脑损伤,后经鉴定为重伤二级。事故发生后,W某驾车逃逸,被途经此处的群众拦截后返回现场抢救伤员。经交管部门认定,W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公诉机关认为,W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致一人重伤后逃逸,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三到四年。W某辩称:自己并没有撞人。
分析
对于“交通肇事罪”,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就犯罪构成而言,该罪的主观方面有特殊之处,即:定罪的主观方面要求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具体要结合行为人对自己的交通违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态认定),而作为法定刑升格情节的“肇事后逃逸”,其主观方面要求为“故意”。所谓“故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的规定,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鉴于定罪、量刑的主观标准存在上述不一致性,律师在为涉嫌交通肇事罪的当事人提供辩护时,务必对该案事实与证据详加审查、认真推敲,充分运用经验法则,准确判断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也就是说,辩护律师在衡量该案证据体系时,对于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要以不同的标准来评估。“过失”的证据足够,不等于“故意”的证据足够;定罪的证据足够,不等于量刑的证据足够。本案的证据并不能确实、充分地证明W某是在“明知”本人已经造成了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
一,关于是否“明知”:对认识因素的考察
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因此,刑法意义上的“故意”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结合。“认识因素”的判断,离不开主观上的“明知”。
本案证据不能确实、充分地证明行为人W某在“撞人”时是“明知”。事发时间是冬日早晨六点左右,刚下过雪,光线较暗、路面很滑。肇事车辆的照片显示:W某驾驶的三轮车曾被自行改装,右侧车窗部挂有拉帘,影响视线;该车辆半新,车斗部位常年颠簸作响,影响听觉,而恰好W某年逾六十,听力不佳。在该车与被害人发生物理接触的“右前部”,没有提取到痕迹物证,双方发生接触、碰撞的程度不深。《现场勘验笔录》、《交通事故勘验照片》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显示:在事故发生后,W某虽然没有立即停车,但是也没有刻意加速逃离或者躲藏的表现,而是沿着公路平直向前行驶。过路群众向其口头告知“撞人”后,W某即停车并赶回事发现场。综合上述因素,现有证据不排除W某对于发生交通事故主观上并不知情的可能。实际上,W某此时的主观心态恰恰是构罪要件中的“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证据仅能证明构罪标准,但是不能证明法定刑升格标准的,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关于是否“为逃避法律责任”而离开现场:对意志因素的考察
证据显示:回到事发地点后,虽然被告人W某坚称自己“没撞人”、“人不是我撞的”,但在问明被害人身份后,其积极联系家人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开车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并垫付医疗费数千元,主观上没有任何迟疑,客观上没有延误救治。在治疗过程中,W某曾因工作原因而离开医院一段时间,但其妻子自始至终陪同救治。W某将单位的工作处理完毕后,又马上返回医院,体现出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从W某的上述行为推断,其虽有离开事故现场的客观行为,但是其主观上并非“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离”。
综上,“离开现场”不等于“肇事后逃逸”。
结论
最终,天津市J区人民法院本着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听取并采纳了上述辩护意见,认定W某犯“交通肇事罪”,但不属于“肇事后逃逸”,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最后,笔者补充说明一点:实际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的规定,“逃逸”既可能影响量刑(“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也可能影响定罪(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为行文方便,笔者侧重于对“逃逸”作为量刑情节的分析。
*本文系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